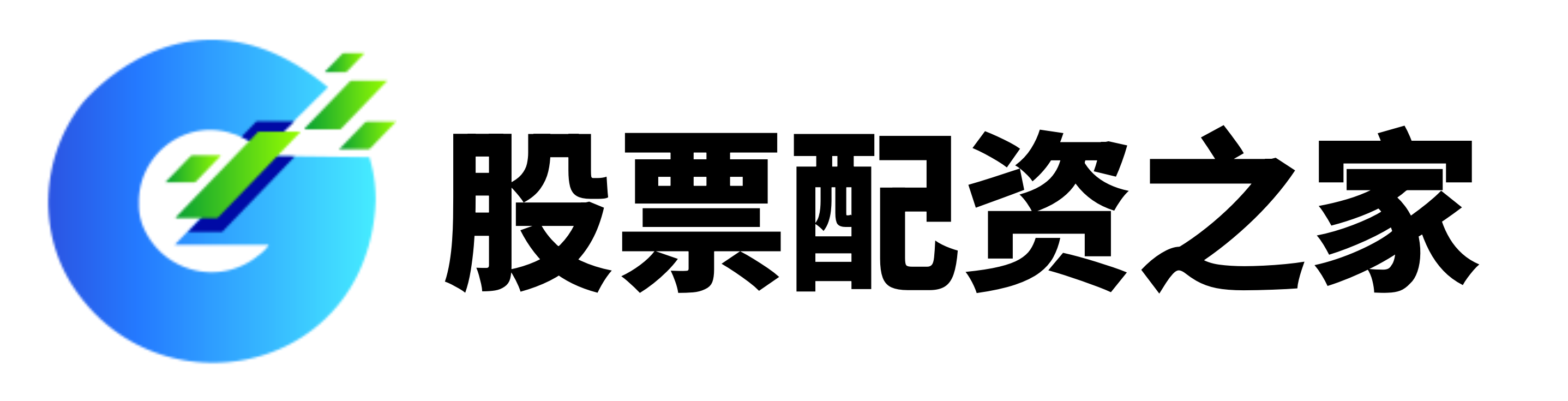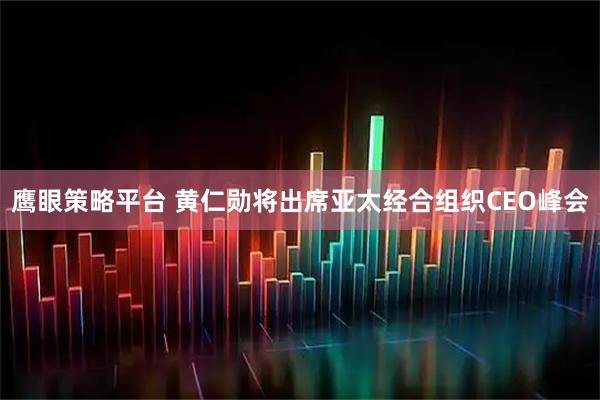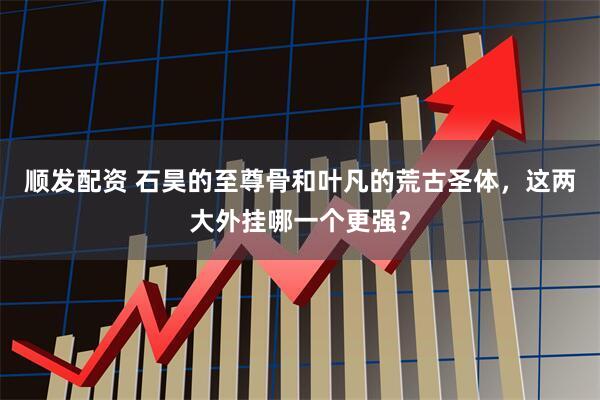银华配资平台 “血誓之弹”的符号学阐释——论《用刀砍我,留下子弹打鬼子》中民族精神的意象化表达

在抗战文学创作中,如何将抽象的民族精神转化为具象可感的文学表达,始终是作家面临的核心命题。张元坤的《用刀砍我,留下子弹打鬼子》给出了极具创新性的答案——以“血誓之弹”为核心意象,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通过其从“生存工具—恩怨见证—信仰图腾—民族符号”的语义嬗变,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意象化转译。从符号学视角审视,“血誓之弹”不仅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道具,更是承载历史记忆、串联个体命运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本文将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解析“血誓之弹”的符号构成与语义演变,探讨其在串联个人与民族、承载创伤与觉醒中的功能价值,进而揭示张元坤以意象系统表达民族精神的创作智慧及对抗战文学的突破意义。
一、“血誓之弹”的符号构成:能指与所指的双重维度
根据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任何符号都由“能指”(物质形式)与“所指”(意义内涵)构成。“血誓之弹”作为作品的核心符号,其能指与所指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叙事语境的变化不断丰富,形成动态的符号阐释空间。
从能指层面看,“血誓之弹”具有明确的物质属性:一颗刻有“金”字的子弹,金属质地的冰冷感、弹头的尖锐形态、刻痕的凹凸质感,构成了可感知的物理存在。这一物质形式本身就带有“暴力”“冲突”的潜在语义,为其后续的意义生成奠定了基础。而“血誓”二字的附加,则为这一物质符号注入了情感与精神的温度——“血”关联着生命、创伤与牺牲,“誓”代表着承诺、坚守与信仰,二者结合使“血誓之弹”的能指超越了单纯的武器属性,具备了情感与精神的暗示性。
展开剩余83%从所指层面看,“血誓之弹”的意义内涵呈现出多层级的特点。在符号学的“直接意指”层面,它是战争中常见的武器,具有“杀伤”“防御”的基本功能;在“含蓄意指”层面,它则承载着个人恩怨、民族信仰、历史记忆等深层意义。这种能指与所指的辩证关系,使“血誓之弹”成为一个“多义性符号”,为其语义嬗变提供了可能性。
二、“血誓之弹”的语义嬗变:从“私人符号”到“公共符号”的演进
“血誓之弹”的语义嬗变是贯穿作品的核心叙事线索,其意义从最初的“私人符号”逐渐升华为“公共符号”,完成了从个体维度到民族维度的跨越,具体呈现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生存工具——暴力与求生的“私人符号”
在寒窑场景中,“血誓之弹”首次出场便被赋予“生存工具”的基本语义。此时的张飞虎与马三刀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粮食、药品)枪口相向,子弹成为决定生死的关键道具。“刻有‘金’字”的细节,最初只是马三刀对个人所有物的标记,带有强烈的“私人属性”。此时的“血誓之弹”,其能指(子弹)与所指(生存工具)形成直接对应,是服务于个体生存需求的“私人符号”,所承载的意义局限于二人之间的生存冲突,尚未与民族历史产生关联。但“银元烫掌”的情节为其语义转变埋下伏笔——马三刀在持枪对峙时留下银元的举动,使子弹的“暴力属性”开始弱化,“人性善意”的意义开始萌芽。
(二)第二阶段:恩怨见证——对立与和解的“关系符号”
随着叙事推进,“血誓之弹”从“生存工具”转变为“恩怨见证”的“关系符号”。寒窑对峙后,子弹虽暂时脱离二人视线,但成为连接彼此恩怨的精神纽带——张飞虎将其视为“耻辱的印记”,马三刀则因留下银元而对子弹产生“愧疚与牵挂”。五原城废墟中“归还子弹”的情节,是这一语义阶段的关键转折:马三刀将保存已久的子弹还给张飞虎,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归还,更是精神层面的“恩怨消解”。此时的子弹,其能指仍为物理形态的子弹,但所指已从“生存工具”转变为“个人恩怨的见证与和解的信物”,完成了从“个体生存符号”到“人际关系符号”的第一次语义跃升,开始突破纯粹的私人领域。
(三)第三阶段:信仰图腾——抗争与坚守的“精神符号”
进入战场语境后,“血誓之弹”的语义进一步升华为“信仰图腾”的“精神符号”。张飞虎带着这颗子弹投身神头岭伏击战、黄土岭战斗等战役,子弹不再是单纯的武器,而是支撑他“残躯卧焦映烽烟”的精神支柱。“弹贯仇魂血一腔”的战斗场景中,子弹的发射不再是简单的杀敌动作,而是对“保家卫国”信仰的践行;“冻土拖残步踉跄”的突围过程中,子弹的存在成为他对抗伤痛、坚守阵地的精神寄托。此时的“血誓之弹”,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物理形态的子弹成为“民族抗争精神”的载体,所指突破了个人恩怨的局限,与“守土御侮”的集体信仰相结合,完成了从“关系符号”到“精神符号”的第二次语义跃升。
(四)第四阶段:民族符号——团结与传承的“公共符号”
马三刀为张飞虎挡下炮弹的情节,使“血誓之弹”最终升华为“民族符号”的“公共符号”。当炮弹袭来时,马三刀扑向张飞虎的瞬间,二人共同守护的不仅是彼此的生命,更是这颗承载着恩怨、信仰的子弹。此时的子弹,其意义彻底超越了个体层面,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曾经对立的个体因共同的民族大义而生死与共,子弹上的“血誓”也从个人承诺升华为“民族誓言”。战后张飞虎“独腿归乡守誓长”,将子弹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更使“血誓之弹”成为承载民族记忆与精神传承的“公共符号”,其意义覆盖到整个民族的历史与未来,完成了语义嬗变的最终阶段。
三、“血誓之弹”的符号功能:串联、承载与建构的三重价值
作为作品的核心符号,“血誓之弹”不仅完成了自身的语义嬗变,更在文本中承担着“串联个人与民族”“承载创伤与觉醒”“建构精神表达体系”的三重功能,成为民族精神意象化表达的关键载体。
(一)串联功能:个体命运与民族历史的叙事纽带
传统抗战文学常面临“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脱节”的问题,而“血誓之弹”通过符号的语义延伸,实现了个体命运与民族历史的有机串联。在寒窑场景中,子弹连接的是张飞虎与马三刀的个人恩怨;进入战场后,子弹连接的是个体战斗与战役进程——张飞虎用这颗子弹击杀敌人,其个人行动成为神头岭伏击战的微观组成;最终马三刀挡炮的瞬间,子弹连接的是个体牺牲与民族团结的宏观主题。这种“以符号为纽带”的叙事方式,让个体命运的起伏始终与民族历史的进程同频共振,既避免了宏大叙事的空洞化,又赋予了个体叙事以历史厚重感,实现了“小我”与“大我”的辩证统一。
(二)承载功能:创伤记忆与精神觉醒的意义容器
“血誓之弹”作为一种“创伤符号”与“觉醒符号”,承载着战争创伤与精神成长的双重内涵。从创伤记忆角度看,子弹上的“血”既是战士的鲜血,也是民族的创伤,“腐肉生蛆”“弹雨穿身”等场景的关联,使子弹成为战争创伤的物质载体;从精神觉醒角度看,子弹的语义嬗变过程对应着人物的精神成长——马三刀从“留下银元”到“舍身挡炮”的转变,张飞虎从“求生本能”到“守誓传承”的成长,都以子弹为见证。这种“符号承载意义”的方式,避免了对创伤与觉醒的直白说教,而是将其融入符号的语义演变中,使读者在解读符号的过程中自行领悟深层内涵,增强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
(三)建构功能:民族精神表达体系的核心支点
张元坤以“血誓之弹”为核心,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民族精神意象表达体系。除“血誓之弹”外,窑洞、老槐树、黄土等意象共同构成了符号网络:窑洞象征“守土御侮”的韧性,老槐树代表“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黄土寓意“扎根大地”的厚重。这些意象围绕“血誓之弹”展开,形成相互呼应的语义关联——窑洞是子弹发挥作用的空间场景,老槐树是子弹传承的见证者,黄土是子弹承载创伤的最终归宿。这种以核心符号为支点、辅助符号为支撑的意象体系,使民族精神的表达摆脱了抽象概念的束缚,转化为具象化的符号组合,实现了“精神内涵—符号系统—文学形象”的完整转化链条。
四、意象化表达的创作智慧与文学史突破
“血誓之弹”的符号学建构,体现了张元坤以意象化表达民族精神的创作智慧,也为抗战文学主题呈现方式带来了重要突破。
在创作智慧层面,张元坤精准把握了“符号的多义性”与“叙事的逻辑性”之间的平衡。他既充分挖掘“血誓之弹”的语义潜能,使其承载个人、民族、历史、精神等多重内涵,又通过“寒窑对峙—战场抗争—归乡传承”的情节链条,确保语义嬗变的逻辑合理性,避免了符号意义的随意堆砌。同时,他将符号学思维与地域文化、人性思考相结合,使“血誓之弹”既有符号的抽象张力,又有文化的具体质感与人性的温度。
在文学史突破层面,这种意象化表达打破了传统抗战文学“口号化”“概念化”的主题呈现模式。以往抗战文学常通过人物对话、作者评论直接阐释民族精神,而张元坤则通过“血誓之弹”的符号演变,让民族精神在符号的语义延伸中自然呈现。这种“以符号代议论”的表达方式,既增强了文本的文学性与审美性,又使民族精神的表达更具深度与感染力,为抗战文学主题呈现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结语
“血誓之弹”作为《用刀砍我,留下子弹打鬼子》的核心符号,其从“生存工具—恩怨见证—信仰图腾—民族符号”的语义嬗变,不仅是推动叙事的关键动力,更是民族精神意象化表达的完整过程。从符号学视角看,这一过程实现了“能指与所指的动态平衡”“个体与民族的有机串联”“创伤与觉醒的意义承载”。张元坤以“血誓之弹”为核心构建的意象系统,展现了他将抽象精神转化为具象符号的创作智慧,也为抗战文学突破“概念化”困境提供了重要启示——民族精神的表达不必依赖直白的说教,通过精心构建的意象符号,同样能实现深刻而动人的传递,这正是《用刀砍我,留下子弹打鬼子》在抗战文学创作中的独特价值所在。
发布于:福建省嘉正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